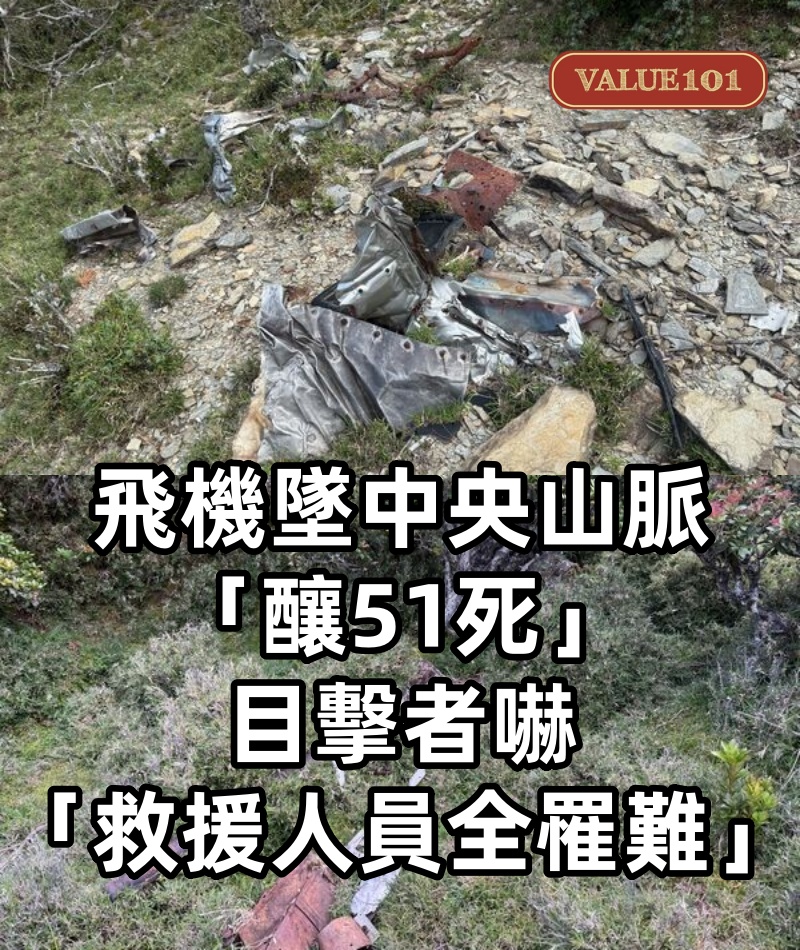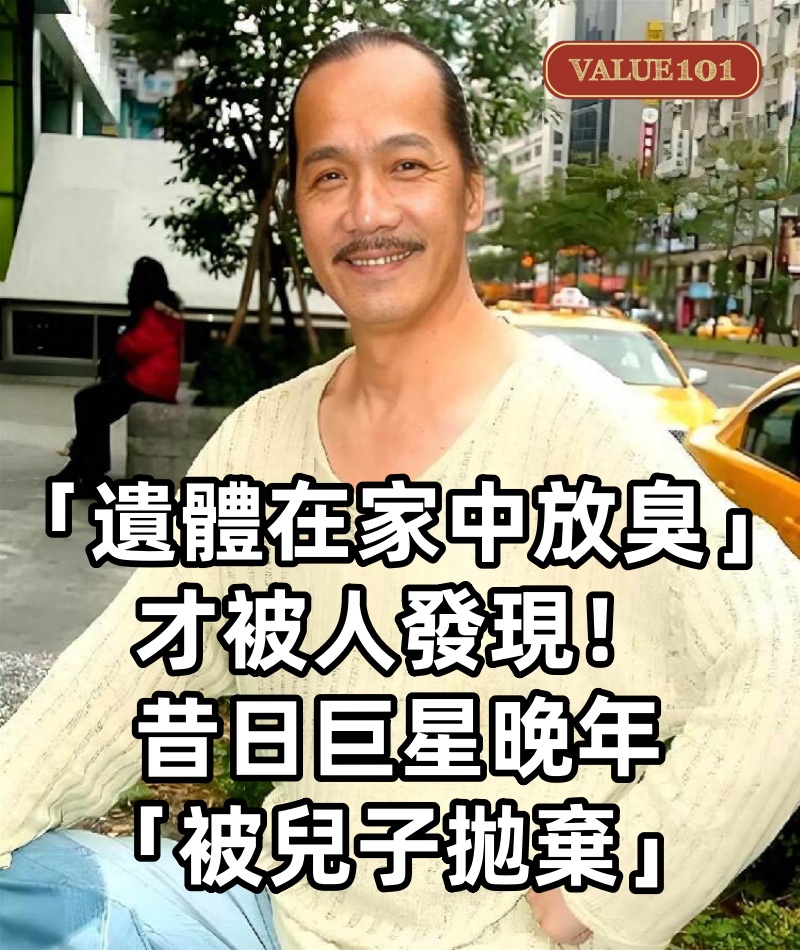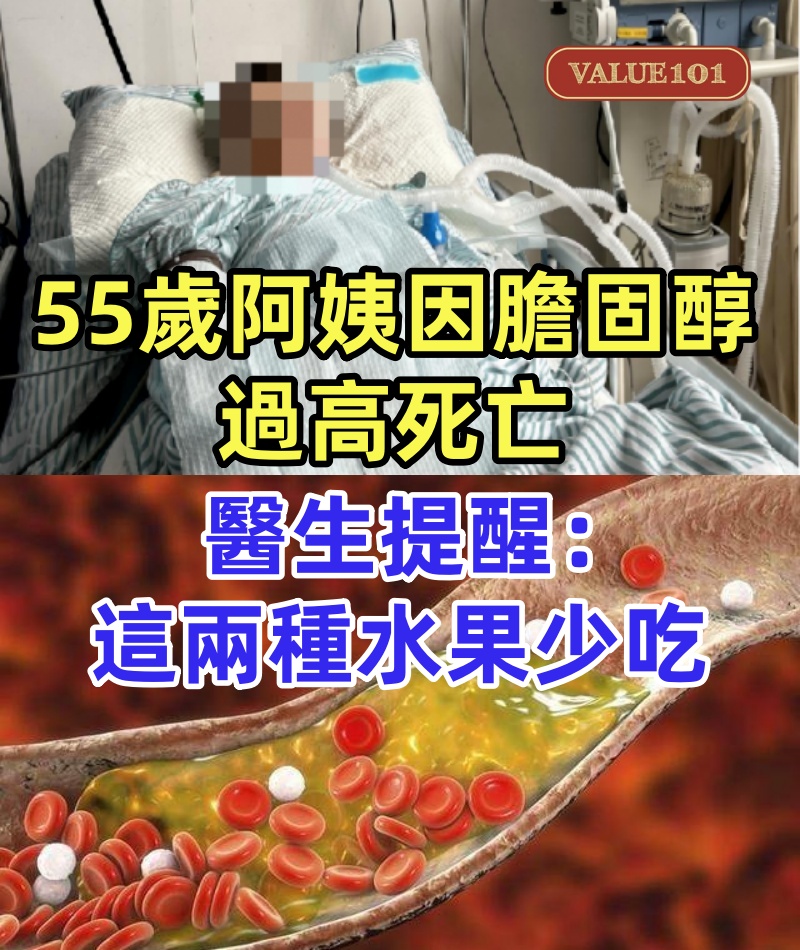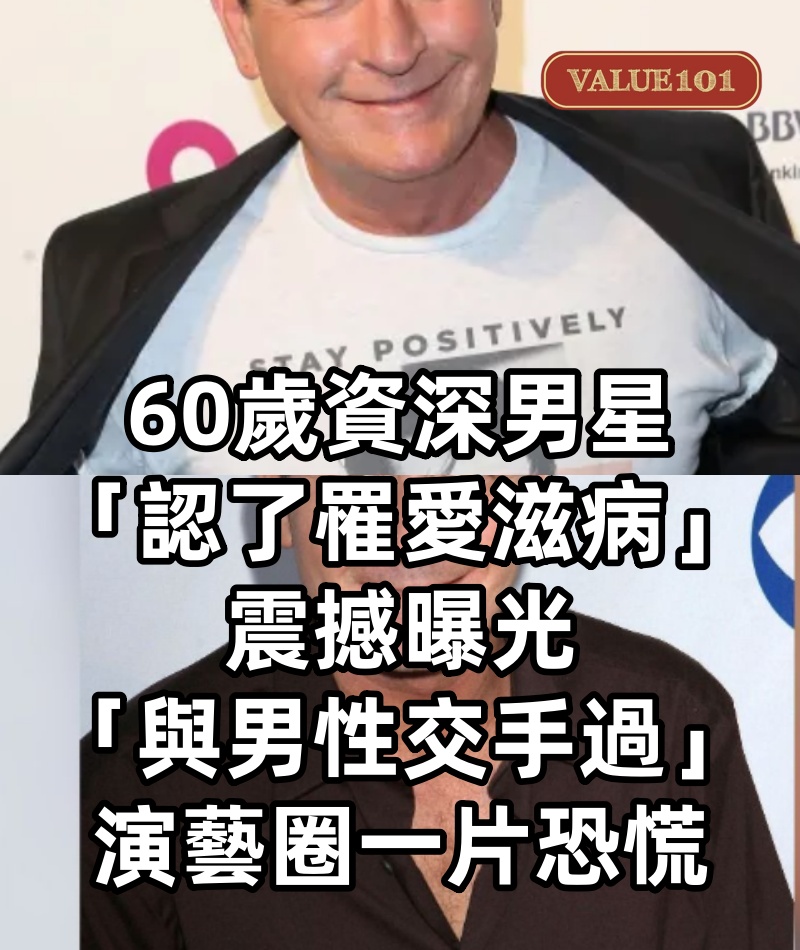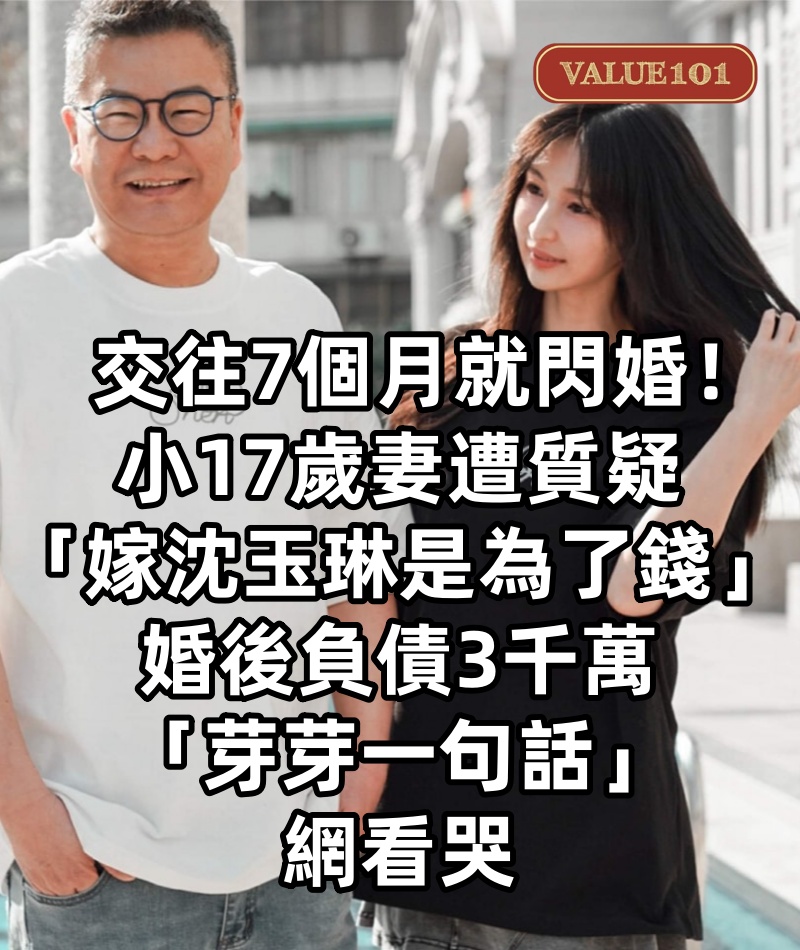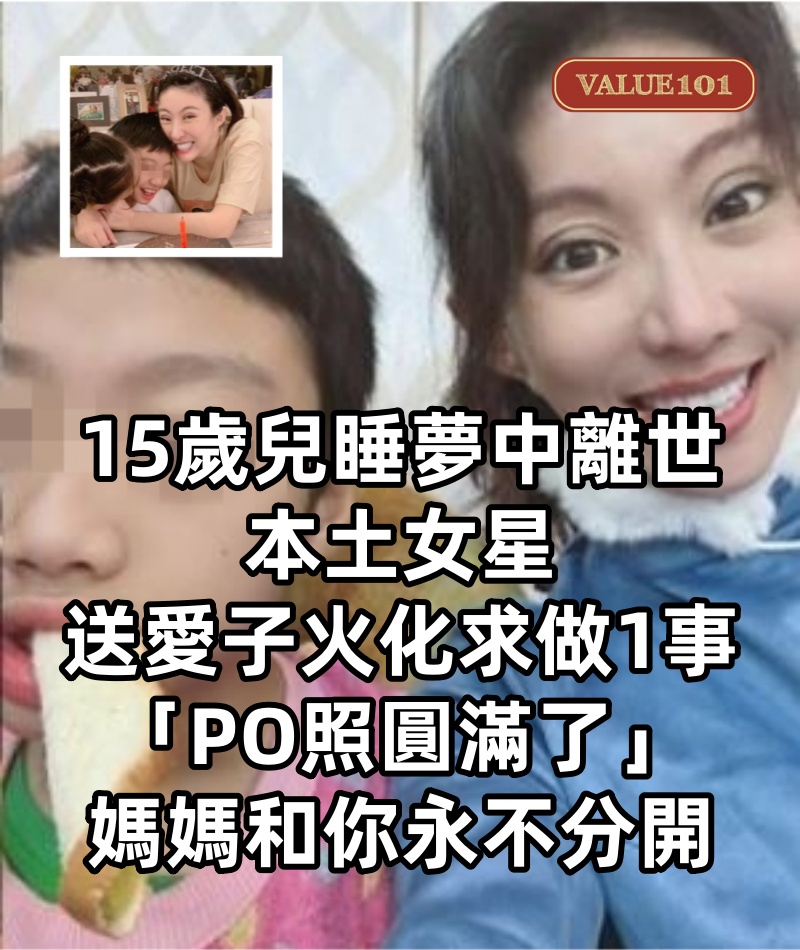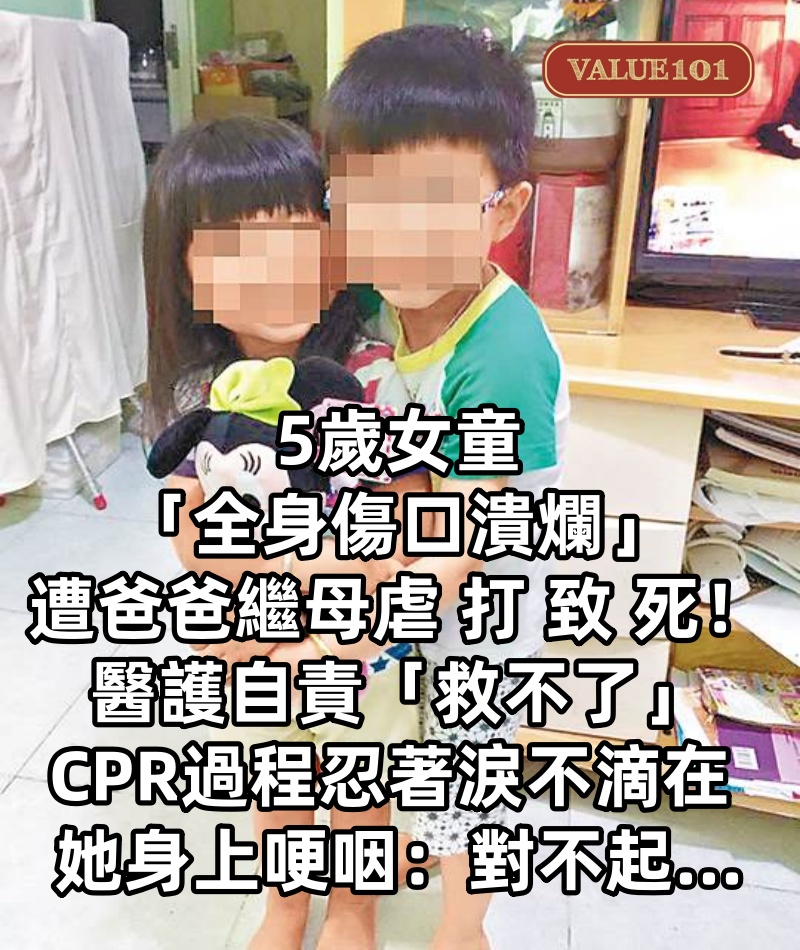看完《皮囊》,才知道活著最難的是什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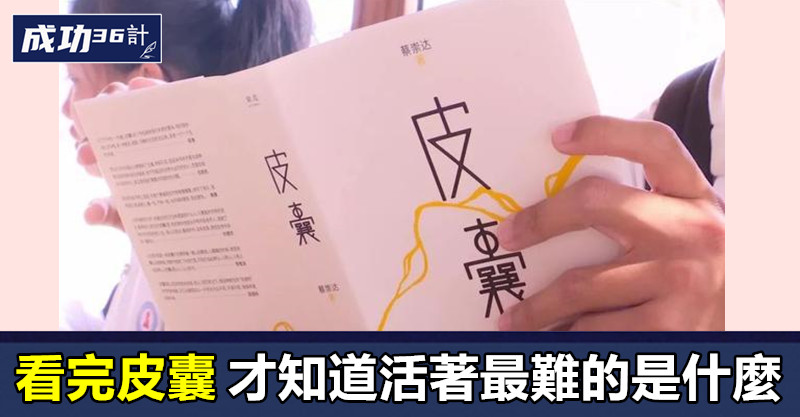
大三這年,蔡崇達成為知名報社的實習生,趕赴北京就職,而厚朴的人生卻走進了一條死胡同。
厚朴的“世界樂隊”解散了,他自己也因為常年掛科,打架鬥毆被學校開除。
分別後不久,厚朴忽然打電話給蔡崇達,希望蔡崇達理解他的困境,帶他去北京闖蕩。
然而,當時的蔡崇達,無法對厚朴的痛苦感同身受,還像從前那樣苦口婆心地勸他做人要踏實。
厚朴指責蔡崇達不懂他,憤怒地掛斷了電話,再也沒有聯繫。
又過了兩年,厚朴終於受不了理想和現實的落差,在無人理解的絕望中,自殺身亡。
或許,厚朴永遠不明白,在這個世界上,沒有人可以對另一個人的傷痛真正地感同身受。
你萬箭穿心,你痛不欲生,也僅僅是你一個人的事,別人也許會安慰你,也許會同情你,但永遠不會真正感受到你的疼痛。
常言道:
不要指望別人理解自己,更不要把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。
人生在世,能理解你的只有你自己,能救贖你的也只有你自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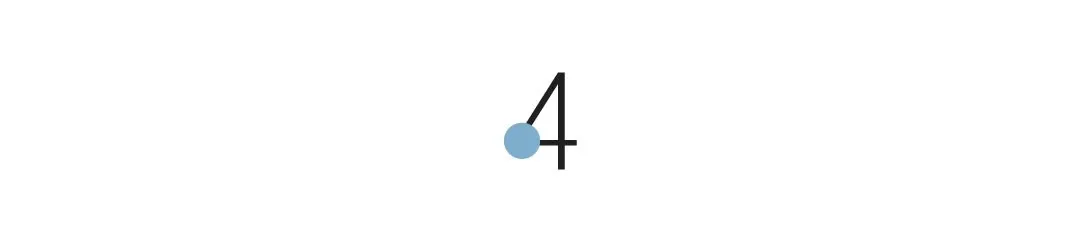
最難放下的是——執念
為什麼蔡崇達拼了命地要賺錢?
在書裡,他直截了當地給出了答案:因為貧窮。
蔡崇達的家庭貧窮到什麼程度?
貧窮到母親不得不半夜偷偷去菜市場撿爛菜葉子,回來煮著吃。
他們的貧窮除了時運不濟,其實和母親執意建房子脫不開干係。
早些年,父母因為超生了蔡崇達這個老二,丟了工作,還被罰了三年糧食。
後來,父親經商屢屢受挫,還在蔡崇達讀高二這年,中風偏癱。
可就在父親剛剛出院後不久,母親卻提出,要加蓋家裡的房子,蓋一座四層小樓。
房子,似乎是母親永遠放下不的執念。
從她結婚那年,她就一直憋著一股勁兒要蓋房子。
無奈,家裡頻遭厄運,房子的事兒就耽擱了下來。
或許是父親的病刺激到了母親,總之,她不顧眾人勸阻,把家裡僅剩的那點錢,都投到了房子上。
最終,房子建好了,生活卻毫無起色。
反而陷入一種僵局,一家人整天為錢發愁,爭吵不休。

這世上的人,大多苦於兩件事:一是得不到,二是已失去。
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道理,可偏偏有人不信,緊攥著那些“想要又得不到”的念頭,折磨自己。
佛語有言:我執,是痛苦的根源。
很多事,你越是想去辦成,越是適得其反;很多夢想,你越是想實現,越是遙不可及。
太過執著的人生,是一場災難;而學會放下,才是活得通透的智慧。
人生匆匆,何必執念太深,隨遇而安,隨緣而活,才是與生活和解的最好方式。
最難看清的是——自己
蔡崇達在《皮囊》的最後,寫過這樣一段話:
“我真正動筆時,才發覺,這無疑像一個醫生,最終把手術刀劃向自己。”
他開始回憶自己走過的路,向我們毫無保留地剖解他自己。
他承認自己走上文學道路的初衷,是為了賺錢,為了撐起那個偏癱的家。
為了拿到獎學金,他從小刻苦學習;
為了給父親治病,他一上大學,就瘋狂打工。
為了省下一點車費,他一年到頭不回家,大年三十還在值班。
有一次,因為疲勞過度,蔡崇達在工作崗位上發燒近40度,一度昏厥。
他拼了命地賺錢,可當他足以帶家人過上好日子的時候,卻陷入迷茫。
他質問自己:你真正喜歡的到底是什麼?你真正享受的是什麼?你到底要什麼樣的生活?
走過人生的至暗時刻,蔡崇達忽然發現,他看不清的,不是命運,而是自己。
為了看清自己,蔡崇達強迫自己慢下來。
他回到故鄉,重走那條斑駁的石板路;他回憶過去,細細品味童年往事;他去遠方旅行,感受異國風情。

最終,他發現,自己依然熱愛文學,真正享受的是為一個個普通人記錄下他們的故事。
當他坐到電腦前,為《皮囊》這本書敲打下一個個句點時,蔡崇達才明白:這正是他苦苦尋覓的感覺。
在希臘的阿波羅神廟前,大門的石板上刻著一行字:“認識你自己”。
生活中,我們總願花更多的時間去揣摩他人,卻很少去探究自己。
而人這一生,最緊要的不是讀懂別人,而是認清自己。
看清自己的理想,看清自己的能力,看清自己到底想要哪種生活,才能為生活找准定位,把控好人生前進的方向。
《皮囊》,是蔡崇達寫給時光的故事,關於苦難、關於理想、關於自我。
他用這些陳年舊事,為我們鑿開了一扇理解命運的大門。
讓我們意識到生活從來困難重重,人生從來苦樂參半,命運從來難以捉摸。
路遙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說:
生活很難,活著更難,人這一輩就是個渡難的過程。
當我們看清生活裡的“難”,只要下定決心,逼自己走下去,必將迎來屬於你的晴空萬里。
與朋友們共勉。